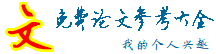摘要:从二战后台湾经济的奠基﹑快速发展﹑泡沫,观察社会环境﹑建筑潮流的改变,探讨重要建筑师的贡献及经济、空间、建筑、文化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台湾,经济发展,建筑发展
1. 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环境的改变
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来,在这个超过半世纪的时间中,我们看到了台湾社会的许多遽变,经济上的成就、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似乎带给台湾许多正面的联想。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快速成长,建筑在这其间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意味着一种生活质量概念的实践,也意味着财富、社会地位的提升,建筑无形之中成为这类高消费性商品的首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台湾社会所期待的现代化,反而成为环境发展上的放任。几乎与经济成长同时开始发生的城乡发展失衡、日益严重的都市化问题,及已达恶劣状况的自然环境保育问题,都使得台湾的正面形象大打折扣,并进而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在经历过八○年代无序的环境发展之后,台湾的整体建筑环境慢慢开始调整建筑的内涵,使其能以具备对环境涵构反省能力的实质创意能力表现为主,而非无中生有的形式操作。
2. 社会环境改变引发不同的建筑潮流
1945年,台湾在被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五十年之后,重回中国之怀抱,重大的改变不仅見之于政治及文化层面,也明显的反应在建筑方面。台湾的建筑发展在日本建筑师主导五十年之后,也重回中国建筑师的掌握之下。
就建筑的发展而言,光复初期的五○及六○年代,台湾建筑的现代性仍以美国为主,大量的西方现代建筑经验与知识透过美国对于台湾各阶层的巨大影响进入台湾,彷佛使台湾进入“美国文化圈”。同时在五○、六○年代政治意識形态也很明显的反应在建筑风格的表达之上。追求或创造一种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曾是1920年代起许多中国建筑师的终极目标,这个时期在台湾政府的支持下宫廷式建筑不断的尝试新的诠释“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意識形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自荣心在作祟,当然有些建筑师的自我使命感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现代建筑在台湾广为流行。大量无地域性现代建筑之出现,固然使整个都市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却也使具有文化特质之台湾都市逐渐失去其地域特质。
从七○年代初起至七○年代末的时间中,台湾历经了战后最大的打击,使得台湾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中,从此,台湾失去了可依凭恃的国际舞台,其国际地位自然不保,因此七○年代末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救亡图存”的想法,积极寻找“出路”,且因为台湾国际地位的变化,对长久以来形成对美国依赖甚深的意识型态已然破灭。七○年代末的本土运动是一个在政治、外交及社会文化孤立无援的情形下所产生的直接反应,其目的并不在于以长久的观点经营台湾,而在于找寻能突破孤立现况的有利工具。七○年代末所提出的本土观点较缺乏自己的论述,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藉西方的后现代论述中对于历史之于现代的宽容,形成了八○年代初台湾在本土建筑上的尝试。整个八○年代对台湾的建筑似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但由于台湾建筑发展异常热络,终于在九○年代初,台湾的房地产发展逐渐萎缩,加上过去诸多人为开发的不当所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愈形频繁,一股反省之声亦逐渐形成一种政策决策所需的共识。然而最坏的年代,或许反而是最好的年代。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建筑界明显可见一股年轻的活力。一群建筑师自1994年起,在宜兰认真寻找理想的家园,“宜兰厝”行动引发的效应至今仍在酦酵;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为数颇众的校园重建规划,带动大批建筑师投入参与,从九二一校园重建衍生的“新校园运动”,从硬件而软件、量变而质变,改变了台湾的教育与学习成长空间;面对全球化经济的同化危机中,“批判的地域主义”也开始敦促人们将区域文化作为有意识培养的而非自生自长的文化运动,更广泛的使用地方设计要素作为对抗全球化的普同性建筑秩序的手段。自1950 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环境与建筑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整体而言台湾建筑运动已从50 年代的“中国传统”逐渐演变至今日的“地域性构筑”。
年代/
社会型态
主要建筑潮流
建筑潮流特点
说明
50 年代
农业
社会

中国传统
地域性构筑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发展源自中国大陆的传统宫殿式建筑。
70 年代以前台湾建筑发展,对西方现代建筑的追求更甚于本土建筑,形成“现代”与“传统”的对立。
60 年代
于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传统宫殿式建筑发展的高峰期。
70 年代
传统工业
受国际环境的挤压,重新思考定位传统。
80 年代
与源自于北美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发展建筑形式上的新本土。
逐渐以自主与自觉的精神形构探索“本土”的建筑。
90 年代
高科技
业
台湾整体社会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重新省思。
21世纪
各地逐渐发展富有地区性环境特色的建筑。
表1 自1950 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环境与建筑的发展脉络概况
3. 建筑潮流中重要建筑师的贡献
从惨淡经营至欣欣向荣,不少有理想抱负的建筑师们为台湾这片土地留下了值得记述的“大地诗篇”,在台湾光复后五十多年的建筑发展中,六○、七○年代留学归国的建筑人塑造了另一股全然不同的建筑风格,作为台湾建筑的先行者,他们或早年在美国获得学位,如王大闳、陈其宽;或是由大陆随国府来台,如修泽兰﹑沈祖海;而由台湾培育再深造者有高而潘﹑陈迈﹑汉宝德﹑吴明修﹑朱祖明与李祖原等。他们亦多半在学院授课,教育下一代的建筑人,在产业与教学都具有深远的贡献与影响。这些多半接受过现代化的建筑教育,或有留学西方的经验,或在专业之余兼职授课的建筑师,他们多元的作品正足以反映台湾多元的文化,他们对于建筑的理念具体影响学子们,这些先行者的贡献,很真实地承载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的建筑发展状况。
五○到七○年代宫殿式建筑在台湾的风行虽然并不是本土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政治力与意识形态介入的结果,但建筑师卢毓骏、杨卓成等人近乎考证式的对中国宫殿式建筑造形的复古,志在“将新精神新材料打入建筑,作为创造新建筑形态的源泉,同时又继起中国传统之文化生命”的建筑也慰藉了来台大陆人士的怀乡情结。
由于台湾早期本土文化的贫乏,一昧的随从现代主义的步伐起舞,从60年代的粗犷主义到70年代的商业建筑,几何量体组合并置放连续的帷幕墙等等。但70年代时期幸有王大闳力行本土化路线,而使得本土化意识慢慢兴起,如孙中山纪念馆为现代建筑加上传统中国的屋顶,屋面上并不铺古典琉璃瓦,而代之以金黄色面砖;屋脊也都经过抽象简化,而结构亦明朗清晰以表达古典建筑鲜明外露之结构系统…等等,但这都只能算是中国风格式的现代建筑。一直到80年代李祖原大安国宅的出现,才挡住了现代主义均一、普同性的、无文化性的浪潮,阻挡了外国主观认定的美学,为台湾本土的文化符码转用到建筑意涵上跨出了一大步,也是台湾后现代的一大步。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